-
查看详情
散文:《石榴红时》
更新时间:2025-11-14
又是一年秋风起,街边卖石榴的摊子渐渐多了起来。每到这个时节,我总会想起奶奶家院子里的那两棵石榴树。
东边那株结红果,花开得浓烈,花瓣层层叠叠地裹着,熟透时“噗”地裂开口,露出玛瑙般晶莹的籽,咬下去,酸甜的汁水在口中迸溅;西边那株结白果,花淡得像月光,五瓣舒展,果皮泛着淡青的白,籽是浅浅的,味道清润些。奶奶常说,白石榴是“素净丫头”,红石榴是个“泼辣小妮子”。我偏爱那“泼辣”的,倒不为它的艳,只为它裂开时那一声轻响,那红得透亮的籽,脆生生一咬,汁水就顺着下巴往下淌,奶奶总举着帕子追着我擦,笑骂一声“小馋猫”。
偷摘石榴,是我和奶奶之间心照不宣的“游击战”。那时我总爱趁她在堂屋纳鞋底,悄悄搬个小板凳凑到树下,先是踮着脚,伸手去够最低的枝丫,指尖刚碰到石榴皮,枝叶就簌簌地晃,惊得麻雀扑棱棱地飞走。后来胆子大些了,便踩着树干上的纹路往上爬,枝丫刮破了小褂,石榴“咚”的一声砸在怀里,也顾不上疼,只顾着把最红最大的往兜里塞。有时摘得太急,石榴掉在地上,奶奶听见动静走出来,也不骂我,只提着竹篮跟在后面,一边捡一边轻声说:“慢些,慢些,树晃倒了,摔疼的可是你。”
后来我去外地上大学,每年秋风乍起,打电话回家,奶奶总在电话那头说:“你那棵红石榴熟了,我给你留着呢,等你回来吃。”放假推开院门,最先看见的就是堂屋桌上的竹篮里用旧报纸仔细包好的石榴。剥一颗放进嘴里,还是记忆里的清甜。只是奶奶的手,不知何时已布满裂口,指节因风湿肿得老高,剥石榴时,偶尔会沾到籽汁。
再后来,老屋要翻修了。推土机开进来的那天,我站在石榴树下不肯走。白石榴树的皮已老得发黑,枝头却仍倔强地擎着几颗青果;红石榴树的叶子还油亮亮的,像一把撑不开的绿伞。工人要动锯子时,奶奶攥紧我的手,低声说:“砍了吧,留着占地方。”可我分明看见,她转身时悄悄抹了把眼睛。
去年清明,我回去了一趟。两株石榴树早已不见踪影,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坑,积着些许雨水。我站在原地,愣了好久,恍惚间,又回到了那些夏天——我蹲在树下吃石榴,奶奶坐在旁边剥花生,阳光透过叶子洒在她银白的发间,把每一道皱纹都染得温柔。
忽然想起最后一次吃奶奶留的石榴,是她生病住院的那个秋天。她坐在病床上,还轻声念叨:“今年白石榴结得少,红得倒甜”。如今超市里的石榴,红的白的应有尽有,我却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也许是爬树时的那份慌张,也许是竹篮里旧报纸的油墨香,更也许是那个拿着竹篮、在树下轻声唤我“慢些”的人。
风一吹过,耳边仿佛还响着石榴叶沙沙的声音,只是回头望去,院子里再也没有那两棵树,也没有那个等我回家吃石榴的奶奶了。
原来最甜的,从来不是石榴籽,而是树下那个等你回家的人。树会老,人会走,可有些甜,会在记忆里越酿越浓,浓成一生都化不开的眷念。(东海农商银行 张楠楠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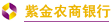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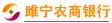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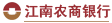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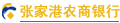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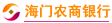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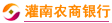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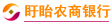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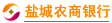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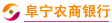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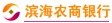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2025年11月14日
2025年11月14日





